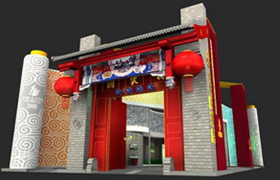李永康人到中年,头脑敏捷,善思考,他的微型小说主题思想有深度,而且文字叙述颇多幽默感,给读者的感觉是老实人说老实话,虽有一点俏皮,但不妨碍它是实在的、真正的“实话实说”,这是作家的本分。入世间,油头滑脑,能编会夸者有也,又有几个出了名,人们言语之间不唾弃其鄙?
李永康是平民作家,既不在商界赚钱又不居官位用权,挤身于平民之间,看平民中的事,听平民中所言,想平民之所想,说平民想说的话,所以他的作品老少咸宜,有多篇作品获中国微型小说学会全国微型小说年度评选二、三等奖;部分作品已译成英、俄文,代表中国优秀微型小说走出了国门。近闻作家喜登“新世纪小小说风云人物榜”,他的微型小说集《红樱桃》列入“最具中学生人气的微型小说名作选”,2008年由北京东方出版社出版。
《红樱桃》是作家的第四部微型小说选集,这本集子除了显示作家广阔、雄厚的生活基础,作品题材直接来源于生活外,同时,让读者更感受到他写作技巧的成熟,艺术含金量更重。他在不断地探索与进步中。人们高兴看到,他的不少作品吸收西方文学成分,如题材形式,主题挖掘等,特别是叙述主体的视角变化:或从小孩眼中看成年人,或从死人眼睛看活人;明明是作家自己写的,却说“这个故事是我向作家提供的”等等,绕了一个圈子,仿佛要避开个人成见求文学的真实性和公正性似的,为他的故事叙述增色不少。作家在其中,作家又不在其中,然而,因为一切感受都源于作家的生活体验与认识,读起来就活泼多了。
作家追求深刻的寓意性
不能把文学与宣传等同起来。就其表现手法考察,文学重寓意,宣传是直白。文学作品传达作家思想感情,是渲染;宣传分析事实真相或阐明一种理论,是传播。文学需要想象,甚至可以虚构;宣传一是一,二是二,来不得半点虚假。法国文学大师左拉说:“一页写得好的书有它的纯洁的寓意,这寓意在于它的完美之中,存在于具有特色的强烈的生活气息里面。” 按传统的说法,寓意和象征是双刃剑,一种景象,一个物体,一个过程,都可以引发人的联想,读书人彼此心领神会,感受自在不言中。这就是艺术趣味,这就是审美享受。听报告和看戏、看故事片和看新闻记录片,是两种不同的接受,一种是美感,一种是被告知。当人们想从阅读中获得美的享受的时候,便去读一首诗歌,或读一篇小说,被一种由文字或情节构造的艺术意境所陶醉,个人感悟由此而生。
《红樱桃》的开卷明第的第一篇《两棵树》,就是典型的寓意性作品。这是一个古老的寓意,作家抛弃了它的原始意义,突出的是现代人的自我激励。用小树比喻人,用薄土比喻人处的环境。既然你处在悬崖上,泥土少,水份不足,活命不?需要面对现实,需要自强不息。怯懦者,贪图享乐者,自怨自艾者,结局是倒塌在风雨中,枉活一次。惟有强者,期求成功者,牺牲小利积累大益者,把所有的营养供给根部,让粗壮的根紧紧地抓住石缝顽强生长。读其文,在潜移默化中,使懦者奋起,使强者勇敢。《生命是美丽的》演绎了同一个道理,只有奋斗者,渴求生命意义者,才会意识到生命是美丽的。他们摆脱困境,克服困难,在追求中,在眼界开阔中,懂得了“没有理想的人像似流水”会被淤泥堵塞。生活中不乏奋进者,但也有不少人安于现状、因循守旧、不期变革者,“周家河坝的人祖祖辈辈都过来了,周家河坝的子子孙孙为什么不能过”?道理总是有的 ,只是从来不承认自欺欺人罢了。他们是经验主义者,不接受间接知识,奉行耳听为虚,眼见为实的机械唯物主义论。大水将桥冲垮了,如果接受这一事实,出门上行五里路,便乘渡船过河赶场,可是他们不信言传,一定要下行八里路,确认桥真是垮掉了,再走回头路八里,再加上行五里,往返折腾共21里,摆渡过河。你说蠢也是蠢,但是他们不认帐,因为他们心中有理论“眼见为实”,理论是正确的,行为是可笑的。《桥》不是实写桥,是用桥表达桥以外的意思,人的愚昧与落后,在科学年代的一种心理脆弱,人为地把桥说成是凶兆。有人从桥上摔下河,纯系偶然;所谓桥基压在龙背上,根本无法稽考。不要你考,他们宁愿把修桥的钱用来在河边修一座龙王庙,“远远近近来烧香许愿跪着磕头的人却络绎不绝”。在无神论的世界,封建迷信抬头,大家心安理得,生活变成荒诞。这样的心态是无法用物质来解释的。《怪圈》是李永康展示发生在我们生活中的穷人与富人的生活反差,形成的两种心态。这两种心态的潜意识,读者要用自己的思考去把握。贫穷的孩子考上大学,因为没有钱,不能鲤鱼跳龙门,那就去闯荡江湖,照样发财。因为他们只需要钱,心态平和。不是么,“镇上的王叔叔、张叔叔,小学都没有毕业,不也成了企业家吗?住洋房,开轿车,拿大哥大”。不要误会作家在宣扬“读书无用论”,恰恰相反,有钱的经理、董事的儿子没考上大学,气得老子暴跳如雷,“你知道不知道老子这一生最抬不起头,吃亏最大的是什么?是肚子里没有多少墨水呀!”经理、董事不差钱,他们就没有亏过。他们说的“亏”是他们自己的另类体验。他们创业不易,摔爬滚打,层层恭维,左右打点,该送的送,该给的给,他们吃过的酸甜苦辣,对罩着他们的那些人的低声下气哈巴狗似的忍受,不是他们的子女应付得了的;面对现实,他们心非木石岂无感。他们那么窝囊,“亏”在那里,心知肚明,不想改变?他们不亏钱,亏的是“学而优则仕”, 经理、董事和企业家们不会将他们的觉悟寄托在儿女身上?生意场上的人,精!投入和产出的利润比例,比谁都清楚;万人之上与万人之下,他们辨析明白。生活中,当官与文凭是紧密联系着的!省、市,县,博士、硕士、学士。何以老板、经理、董事对娃娃考不上大学,如此愤怒,如此暴跳如雷,如此心态不平和,读者自然明白了。小说发挥了它的艺术表现力,作家内心的潜台词,醒人心脾的寓意,在文字外,不在文字内,不言亦言。
《酒干倘卖呒》中的老人,因受旧酒瓶伤害,为了不让旧酒瓶再伤人,自己开家收购店。蚀本也干。听说酒厂在报纸上表扬他,要请他当厂里的特别顾问,要和他联营收购用过的啤酒瓶,“他猛地一拳砸在桌子上,气愤地说,这是软刀子杀人”!什么意思呢?这引起读者的思考,——是不是“吃人口软,拿人手软”?对,读者豁然开朗,有了懂得歇后语似的快感。读者对一篇(部)文学作品“努力理智认识它,深入发挥它的实质。这样,它的珍贵涵义就会展现出来”了。
作家在幽默中展现荒诞
李永康言谈的幽默,赋予了他做文章的语言的幽默,他的幽默有些苦涩。在他笔下,有人的荒唐,有情节的荒诞。《岁月》中的两口子意见与感受始终一致,却偏偏闹着要分手,言语中仍不失柔情蜜意,荒唐不?死了的贪官能说话,还要评说人事,表达思念二奶和拿人钱财,未于人消灾的内疚;坐在办公室的主管的脑袋掉进了废纸篓,一大群苍蝇叮在上面,这贪官念念不忘当年在政界的风车斗转;《死因不明》中的四个字就把一个老人当场吓死,来的是哪方神圣?一个年终大会正在进行,主持人竟然宣布开始玩《吹气球游戏》,那成百上千的气球“啪啪啪”的爆破声,让大家开心,又代替了新年将到鞭炮驱逐“年”的不吉祥的凶兆。如此这般,荒诞不?在李永康笔下,人醉心于物质主义,受到调侃,失去自我尊严,遭到嘲笑。对人的荒诞与荒唐,作家毫不留情,挖苦殆尽。荒唐离荒诞一步之遥,也是作家褒贬时世的切入点。作家本人事事关心。在荒唐人的身上,读者可以发现自己,文章的教化便在其中。
人生下来不是恶习缠身,但是在后天大环境的熏陶、污染下,他会变得世故、圆滑,心与口不一。一般人生存意识很强,可是每每放弃了生活的高尚。物质保证人的生存,精神提高人的生活。求生存的人总是营营碌绿,四处钻营。不过很多人的生存方式掩盖在亲情友好的幌子下:送你一个礼,给我弄一笔生意,或者谋个职位;或者你用你的权,我用我的钱,你喊我小弟,我叫你大哥,用关系将工程拿过来。你喝香的,我吃辣的,大家发财,都是好人。生活中请客送礼的“人情文化”形成了办事的环节,彼此都敏感,人也变得忒势利。《深夜来客》可以视为李永康另一篇作品《挂历》的反衬。《挂历》是主人敏感,看见别人放在沙发上的东西,就以为是送自己的。这家主人还好,告诉客人,既然是朋友,要办事也不必送礼;《深夜来客》是客人势利。深更半夜一位客人因是听错了一句话,以为这家的男人“高升”是升官了,于是送水果来拉关系,来巴结。当从主人口中弄清楚“高升”是指他的妻子生小孩时,客人一下明白,搞错了,送了不是白送?于是自我解嘲地说道:“你真会开玩笑。你升了官,哪个就来找你开后门嘛!好,不聊了,我要回家了,小娃娃得病,上街一趟顺便称几斤水果,你尝一个吗?嗨嗨嗨!”客人自我解嘲,化险为夷,避免了钱财损失,可是这一跌宕的情节,将荒诞中人的心灵丑恶暴露无遗。人在求生存中惶惶终日,雨果说“动物生存,而人则生活”,悲乎?
《代价》更把人的无聊写得淋漓尽致。张三李四王五三个朋友,为了找到他们心仪的饭馆,穿小街,走窄巷,一家又一家,“腿走酸脚走软头上走得直冒汗肚子走得像刀片”,仍然没有吃到“正宗”的。什么是正宗的?好吃嘴们说不出子丑寅卯,“吃了就知道了”,于是打的七八里到另一镇再找“渣渣面”。满街是正宗的,老字号的,老牌子的,还有老牌正宗老子号的,正宗老字号老牌子的,目不暇接,他们“从街的这一头走到街的那一头”,最后进了一家省报表扬老板助人为乐的面馆,可是这“渣渣面”没盐没味,不过,安慰自己,三个人统一说法“是还是有它的特色”,坐着人力车回家时“已是半夜”。荒诞在于,想要的,并不是他们真正了解的;见到了,又辨别不出真迹与赝品。心中无数又要冒绷内行。无论人们说时间就是金钱也好,或说时间就是生命也罢,反正,有的人就在吃吃喝喝中浪费岁月,消磨意志。在讽刺中的李永康告诉读者,幸福可以被庸俗,时尚可以变疯狂。
《证据》的荒诞就在于没有证据。既然白毛猪儿家家有,玉成嫂凭什么说金二嫂家的猪是她家的猪?批评要注意政治,说话要有证据。既然没证没据,想“胜利”就要靠自我论证的智慧,或者叫做鬼心眼儿。金二嫂提出了一个虚假前提:猪把她掉在猪槽里的金坠子吞了。玉成嫂怀疑她在扯谎,怎么证实呢?金二嫂放话:把猪杀了,破肚开肠。说杀就杀,猪肠子也被拉出来了。真的将金坠子拿出来,咋办?不见金坠子,后果会如何?这个时候两人较量的是心理毅力,或称心理承受力。终于,金二嫂的“理直气壮”的气势吓退了“觉得她在扯谎”的玉成嫂,于是“玉成嫂捂着鼻子,偷看了金二嫂一眼,脸色惨白地挤出人群”。“金二嫂见玉成嫂一溜走,也悄悄地笑着回家去了”。这就是现代版的“假作真事真亦假”!作家的系列作品揭示了这样一个事实:世间事无奇不有,多少荒唐人,多少荒诞事。
思考型的叙事层面
微型小说,从阅读时间看,它是快餐文化,但需要读者慢慢咀嚼,还得学会思考。没有思考的文化是可悲的。作者正是从思考角度出发,对他的叙事层面作了精心设计。可能有的读者在读完李永康的某一篇小说后,一时半会还理不清它的故事结局的因果关系,或要说明什么。不过,只要你回过头来,在他的字里行间去理解它的某些文字或某个句子的含义,你能恍然大悟,原来这样。所以,我们把李永康的叙事结构分为情节层面和话语层面。话语,有作家的话语,有人物的话语,是理解作品的关键词。
比如我们上面提到的小说《证据》,它的情节是:两个女人争吵猪是我的,咋验证?一方说破肚开肠,先后两个女人都离开了现场,然而,热心肠的人们还在那里帮着仔细寻找证据。结局是什么呢?我们引用了这篇作品中的两段文字,意在提示读者咀嚼它的意思,真真假假就一清二楚了。情节吸引你,字里行间的话语揭开迷,你得到了阅读欣赏的乐趣。
《五奶奶》的故事更如此,你不去认识、了解并理解它的话语,你就不易读懂它。故事情节层面是说,五奶奶有三个儿子,都有出息,在城里工作,把五奶奶接进城住,不久,五奶奶一个人回来了。尔后十天半月进城一次,三二日便回来。有一天,五奶奶到另一个世界去了,儿子没有回来,是山里的人厚道,你几斤米,他几根木料,我出几十块青砖,“隆重地安葬了五奶奶”。故事完了,读者心上没有疙瘩吗?老人去世,儿女尽孝必归,况乎距离只是城里与城外之遥,可是儿子一个也没回来。是儿子不孝?不对呀,因为五奶奶说:“瞎猜疑要烂嘴巴的,我儿媳对我好得没法说。”既然那么好,怎么去了两三天就回来?儿子有出息,干吗老人生前要上山割一种辫绳子的梳梳草卖以维持生活?死的时候依然身无半文?作者当面问过老人回来的原因,“她不肯说”。有人说她有福不会享,她也不争辩。其实,从这些字里行间,人们已经明白,老人的善良——不说儿女是非,可怜天下父母心,她是一个不幸的人。大家相处得不好才回来,但她不肯说,你说准了,她否认。她还要不时穿上洗得泛白了衣服进城住上三两天,为儿媳保持体面。正是作家的话语交代中,让她的三个儿子使我们寒心,对比之下,使我们充满了对五奶奶的敬爱之情。
《机会》告诉读者的是什么呢?作者设计了A与B不断的想做一笔生意又错过机会的情节,没有作任何对与不对的评说。在末尾,作家写道:临终时,A与B遗言是,“只有来生了”。作者说“A和B的遗言没有人能听明白”。真的吗?作者虚晃一枪,制造阅读的迷局。从文字上看,A和B彼此缺乏的是信任和诚恳。事情还没有开始,他们就担心“这笔生意多半要泡汤”,丧失了行动的决心,可出门,可不出门,犹豫;想约见也可不约见,懒洋洋了。彼此不齐心,“A到B那里扑了空,B到A那里同样扑了空”。信任不建立,疑心不排除,纵然希望千百次,他和你,你和他,临终遗言仍然是“只有来生了”。一部文学作品用文字揭示的意义才是隽永的,虽然情节给了你以乐趣。情节是一个人的体态,话语是一个人的活力。当与人相处时猜疑心太重,会一事无成。
耐人回味的是小说《蛙声》,写一位夜间睡在高楼稠密的城市宾馆里的房客,听见一片蛙声,清脆、明亮,不绝于耳。开灯一看,除了灯火,便是寂静。告诉服务小姐,有蛙声,回答他,神经病!可能他有神经病,因为他能听见卫生间的滴水声模仿了蛙声。这是他的幻觉与向往:蛙声中,“这里真清净”,月光下,池塘边,菏叶青青,“莲花开了”,“蝙蝠和蜻蜓”,还有“情侣”。作者问,“是水复活了记忆”?还是人生成的幻想?以前,这里是成片良田,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在蛙声中睡着,又在蛙声中醒来。人对蛙声有特别的感情,人说关心蛙声就年轻,作者问,“那与蛙声为邻呢”?作者的话语,传达出现代物质文明与自然环境中的生物、植物、动物应保持的和谐、共存的生态意愿。反映了群众的声音。
《沧桑泪》和《天麻》两篇小说,在作者的情节层面下的话语层面中,对两种人性丑陋给予了无情的鞭打。一个是我说了算,“我说他是瞎子就是瞎子”,尽管这是假话;一个是为了掩饰自己的私心,编造假话,“掩耳盗铃自欺欺人”直到今天。古人云,一日三省吾身,意在教人发现缺点,改正错误。世间事物,包括人在内,总在不断否定自己中自我完善,获得新生,不断前进。但有人为了体面、形象,乐意生活在谎言中。他口头的内疚,并不一定说明他心悦诚服。
读李永康的微型小说,人们会感受许多,正如作家在《误读》中说的,“读小说可以让人回归自己,也会让人离自己越来越远”。读者在文学作品中吸取养料,不像婴幼儿,听凭他人喂食,成人要用思考鉴别有益或有害,就回归自己了。
2009年7月31日改毕 · 成都
(原载《成都大学学报》2011年4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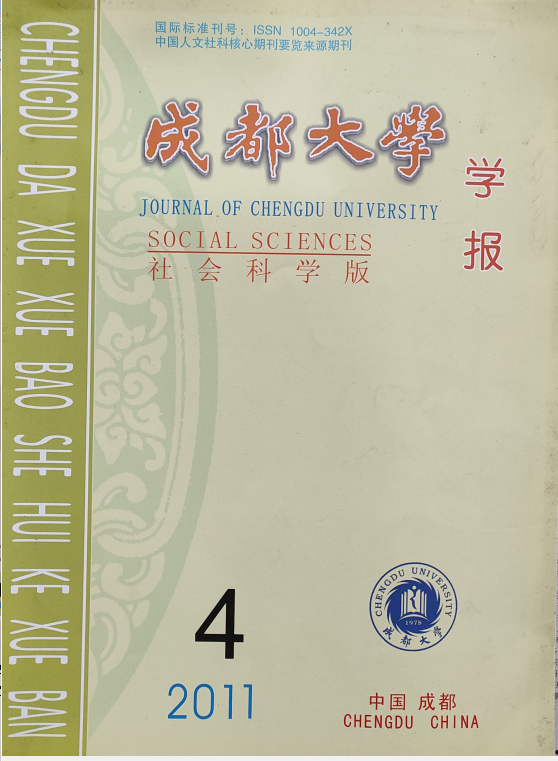
刘连青(1937——2017)成都大学教授,原成都市微型小说学会秘书长。译著有《希腊罗马神话故事》(四川文艺出版社2015年7月)《正确解读(娜娜)和它的作者——重评左拉和他的自然主义文学》(成都时代出版社2011年9月)等。
- 1 温江区文化馆2021年公共文化数字化平台运营及维护服务项目 评选公告
- 2 2025年温江区文化馆市民艺术培训学校(留位艺术夜校)培训服务采购项目 评选公告
- 3 成都市温江区文化馆(美术馆)2025年保安服务采购项目结果公示
- 4 成都市温江区文化馆(美术馆)2025年保安服务采购项目评选公告
- 5 温江区文化馆2024年公共文化数字化平台运营及维护服务项目结果公示
- 6 温江区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目录及 项目代表性传承人 (2024年版)
- 7 温江区文化馆2024年公共文化数字化平台运营及维护服务项目评选公告
- 8 2024年温江区文化馆市民文化艺术培训学校服务外包项目结果公示
- 9 “成渝地•巴蜀情”——“成渝德眉资”文旅交流联动暨2023年“成都文化四季风•音乐消夏”少儿才艺大赛五城市总决赛我区7人获奖!
- 10 2024年温江区文化馆市民文化艺术培训学校服务外包项目评选公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