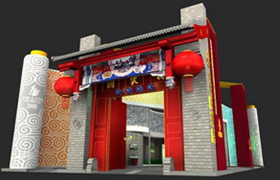李永康说:“我写小小说,是因为此乃是我要做的非同一般之事情中的一件”(见其小小说集《小村人》“代后记”)。从这句话里可以看出,他不是抱着“玩”的心态来创作的,他是把小小说当作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件事情,当作他生命里的一种追求。所以,正如作家罗伟章评价的那样,李永康从不乱写什么。在浮躁之气笼罩着的日益功利化的文学生态中,他则平静地,扎扎实实地写着他钟情的小小说。这样的态度怎么可能创作不出优秀的作品呢?《生命是美丽的》、《十二岁出门远行》、《红樱桃》、《老人与鸟》等一批小小说佳作在李永康的笔下源源不断地流淌出来,那实在是太自然不过了。
从内容上讲,李永康多是书写社会和人生中美好的一面,从而去展示人性中的真与善,让人们在关怀和温暖中体味生命的美丽。如《酒干倘卖唔》,它以一个老人近于“神经质”的行为,表现了个体生命的被珍视和被维护;再譬如《红樱桃》,文中那个纯真、无邪的小男孩肯定会在我们的心底挥之不去,因为他就是“真”的象征、“善”的化身;最具代表性的一篇当然要数《生命是美丽的》,这篇被广为传播的小小说确实是难得的优秀作品。尽管文章的基调有些沉重,但它散发出来的依然是清新俊朗之气。它告诉我们,生命的花朵从不因贫穷而干枯,向着美丽绽放是生命之花的本质所在。类似的作品还有《小村人》、《将军树》、《迟到》等。
李永康为何把笔墨多放在对社会和人生中美好的一面书写上呢?原因可能有很多。但我想,其中一个多少会与文体意识有关。笔者曾在一篇文章中,把小小说比喻成小说森林中的香樟树。意思是说,小小说也有类似于香樟树的功能:散发香味和驱虫效用。由于小小说的受众群体主要是青少年(以中学生为主),所以它应更多地表现真善美,从正面唤起他们对美好生活和美好事物的追求。如果过多传递人性中阴暗的东西,对尚缺少辨别能力的学生来说,很可能会是一种无意的伤害。我想,李永康肯定比笔者更为明白其中的道理。当然,这并不是说李永康完全不去表现社会和人生中丑恶的一面:《胡屠夫出书》、《挂历》就是对商人和为官者在金钱和权力下被异化的绝妙讽刺;《地球还原公司》则以大胆夸张的方式表达了作者对地球被人们的现实利益日益侵蚀的深重忧虑;粗读《中国传奇》,我们可能会对这篇作品的标题莫名其妙,甚至会认为有点“题不对文”。但倘若仔细揣摩,我们便会发现作者的匠心之处。《中国传奇》的创作起因应该是源于大多数中国人的生存压力,但作者越过这一层面,他想表达的,是对中国人盲目幻想、不脚踏实地的生存心理和文化性格的批判。读此文,我想起了柏杨的《丑陋的中国人》。我觉得,二者有异曲同工之妙,一是真实描绘,酣畅淋漓;一是科幻虚构,委婉含蓄。
从艺术技巧上讲,李永康的小小说多采取写实的笔法,经由线性叙述,使得故事清晰,有始有终,人物鲜明,阅读起来十分流畅。当然,也有一些作品例外,如《失乐园》。这是一个存有多义性主题的小小说文本。它蕴含着禁锢与反抗,也蕴含着城市对乡村的侵蚀,当然更蕴含着作者对生态破坏的忧虑。在写法上,它看似写实——精细入微地描写蚂蚁的日常生活,其实,这是一篇虚写的作品。它是借写蚂蚁来写人,借蚂蚁生态环境的破坏来写人类的生态环境的的破坏,借蚂蚁失去了欢乐园来写人类失去了欢乐园,通篇充满着隐喻。由此篇作品再联系《中国传奇》等,我隐隐地感觉到李永康的创作进入了一种崭新的状态:由写实到虚幻,由刻意到自然。这种状态是一个作家不断前进的标示。
下面再来说一下李永康的小小说评论。在1996年第5期的《青年作家》上,作家李永康发表了《小小说的创作呼唤大手笔》一文。在这篇文章里,李永康指出:重复已有的成果是小小说创作的一个误区,也是小小说缺乏大气磅礴的立意的致命缺陷。据说刚刚开始创作小小说不久的侯德云看了这篇文章,产生了很大的精神压力。
除了撰写文艺随笔为小小说摇旗呐喊,李永康还策划并亲自操作了杨晓敏、许行、王奎山、谢志强、凌鼎年、罗伟章、滕刚等十多位作家的访谈。作为一种系列成果,这些访谈以《为了一种新文体——作家访谈》之名于2007年2月由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在小小说领域产生了巨大反响,并在整个小说界也产生了不小的轰动。
李永康的系列作家访谈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它探讨的是有关小小说的重大问题,如小小说的立意,创作数量和质量的关系,大陆小小说存在的不足,海外华文小小说的发展现状,小小说金麻雀奖的设立以及小小说能否进入鲁迅文学奖等,而对小小说的创作技巧、技法等具体、细微的东西,李永康则很少涉及。这固然是因为千变万化的技巧、技法很难在短的篇幅里剖析透彻,更重要的因素是上述问题直接关系到小小说的生死存亡。需要特别提及的一篇访谈录,是对杨晓敏先生的访谈。在杨晓敏先生的《小小说是平民艺术》面世后,李永康对此是异样的惊喜,同时也感到不满足,在访谈录中,他说,平民艺术的概念太宽泛了,小小说的独特性又在哪里呢?杨晓敏先生的回答是极为精彩的。这就是《再论小小说是平民艺术》的催生。小小说是同时具有三种艺术功能的文学品种:即大多数人都能阅读,大多数人都能参与创作,大多数人都能从中直接受益。今天这个论述被广为引用。可以说,正是有了这样的回应和诠释,“小小说是平民艺术”的理论才得以不断地补充和完善,并日渐在人们心中生根发芽。
二、作者的态度是真诚而严肃的。在每一篇访谈的字里行间,我们都可以强烈地感受到,李永康的态度是极为真诚的,他始终像朋友一样不断地肯定(不是附和)着被访谈者,并对被访谈者(如陈永林)遭受某些非议表示理解。这是一种多么良好的美德啊。当然,肯定别人并不意味着无原则的夸奖或吹捧。在关涉到小小说文体的重大问题上,李永康是严肃的。有时因为意见相左,他会撕下脸面据理力争。如对王奎山提出的“读书是一件十分危险的事”上,李永康就以茅盾、王安忆、张炜为例加以反驳。
三、作者的视野是宽阔的。虽然是就小小说文体展开的访谈,但作者并不把问题局限在小小说上。因为,作为一个作家,李永康深切地认识到,倘若把小小说封闭起来,那么这种新文体就永远不会有成熟的那一天。所以,在访谈中间,除了引用我国短中长篇小说作家对创作的见解,他还多处引用格里耶、黑井千次、卡尔维诺和《小城畸人》、《米格尔大街》等外国的作家、作品来展开论证。这不是卖弄,这是一个作家和评论家为了文体建设不断努力的体现。
无论在小小说创作还是在评论上,李永康都取得了不俗的成绩。我相信,今后他会有更大的突破。
原载《当代文学格局中的小小说》 雪弟 著 大众文艺出版社 2012年12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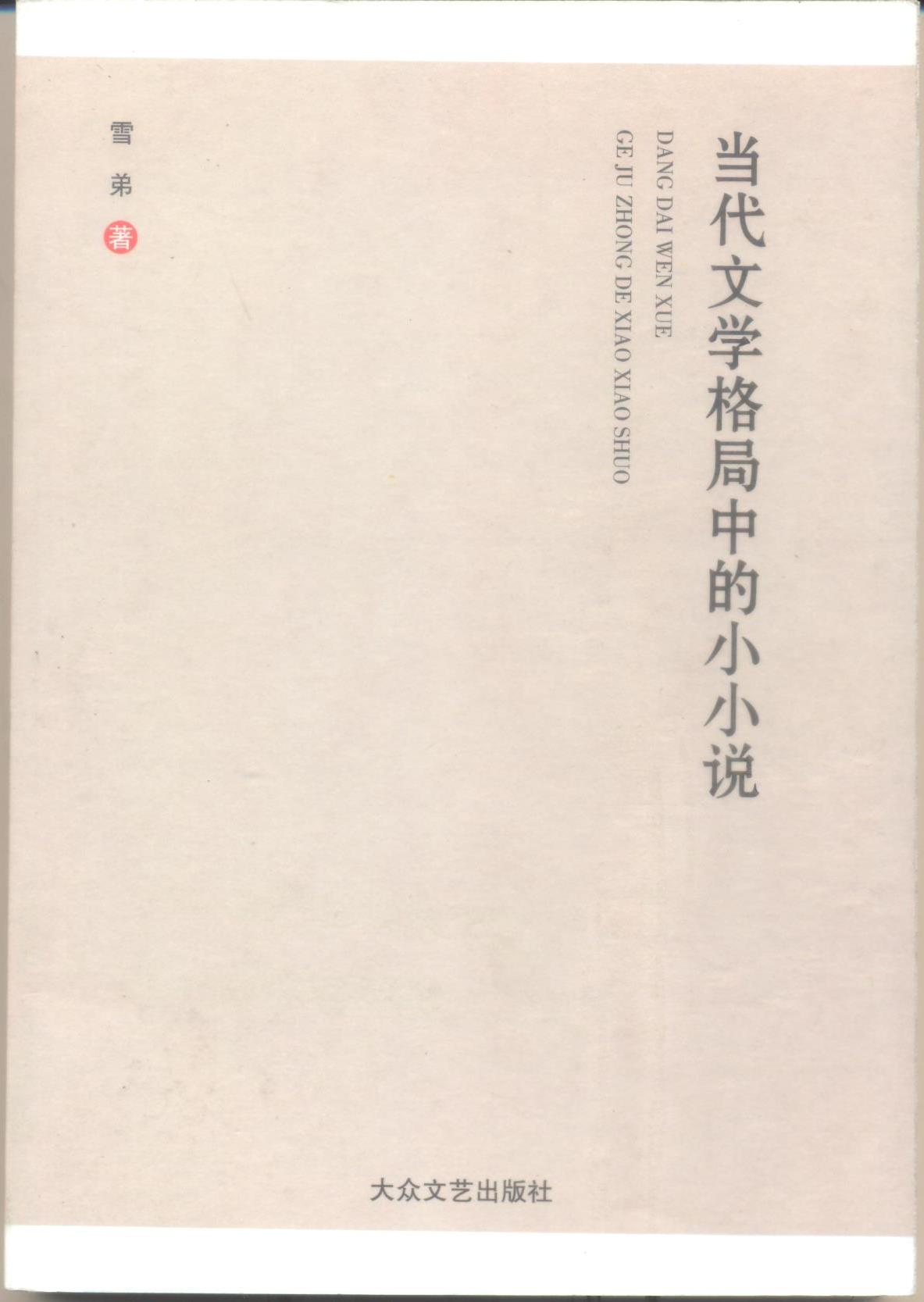
《当代文学格局中的小小说》 雪弟 著 大众文艺出版社 2012年12月
- 1 温江区文化馆2021年公共文化数字化平台运营及维护服务项目 评选公告
- 2 2025年温江区文化馆市民艺术培训学校(留位艺术夜校)培训服务采购项目 评选公告
- 3 成都市温江区文化馆(美术馆)2025年保安服务采购项目结果公示
- 4 成都市温江区文化馆(美术馆)2025年保安服务采购项目评选公告
- 5 温江区文化馆2024年公共文化数字化平台运营及维护服务项目结果公示
- 6 温江区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目录及 项目代表性传承人 (2024年版)
- 7 温江区文化馆2024年公共文化数字化平台运营及维护服务项目评选公告
- 8 2024年温江区文化馆市民文化艺术培训学校服务外包项目结果公示
- 9 “成渝地•巴蜀情”——“成渝德眉资”文旅交流联动暨2023年“成都文化四季风•音乐消夏”少儿才艺大赛五城市总决赛我区7人获奖!
- 10 2024年温江区文化馆市民文化艺术培训学校服务外包项目评选公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