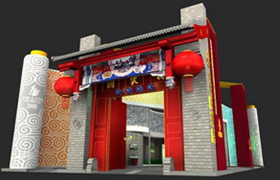多年来,李永康一直“钟情小小说”(见其随笔《钟情小小说》)。对小小说的“钟情”,使他不仅沉浸在小小说的创作中,也沉浸在对小小说的文体特征、艺术创新、现状与发展等问题的思考中(见其有关小小说的系列访谈和随笔)。按照一般的理解,这种“钟情”和互动式的沉浸,一定会催生出大量的作品来,然而纵观李永康的创作,却没有年产百篇甚至几百篇的现象出现。李永康写得很沉稳,这和眼下小小说界某些作者被升腾而起的浮躁之气所包裹的写作是很不相同的。在文学创作活动中,沉稳并不是愚钝,而是一种对生活和题材更内在的感受和消化,所以一般来讲,沉稳的写作是更接近心灵感受的写作。李永康对沉稳的坚守,以及他动笔大都基于“首先是有什么撞击了我的心灵”(李永康小小说集《小村人》后记)的进入方式,使他的小小说虽然总体数量并不庞大,却留下了不少打动读者心灵的作品。在这些作品中,我们能明显地感受到那一团团氤氲在文字里的关怀和温情--从更实质的角度来看李永康的小小说创作,我们会发现,他一直是在用关怀和温情写作。
虽然李永康也写过《关于小小说的小小说》、《探监》、《20世纪末小小说界一场将起未起的官司》等具有实验意味的小小说,但整体来看,这些实验小小说并不构成其创作主流。让我们对其作品感触良多的,还是《生活》、《五奶奶》、《老人与鸟》、《生命是美丽的》、《杀人者》、《红樱桃》、《沧桑泪》、《酒干倘卖呒》、《二胡的悲剧》等一批触及人心和人性的作品。这些作品,都在平实的文字中散发出了深切的关怀和温情。这种关怀和温情有世俗倾向的(如《酒干倘卖呒》、《五奶奶》等),但更多却是人文倾向的。这些具有人文倾向的关怀,在《生活》、《老人与鸟》、《生命是美丽的》、《杀人者》等作品中都有着不同程度、不同角度的展现。《生活》中“我”对王玉梅的命运的关注、王玉梅在同学们的同情和关心中的出走以及王玉梅最后的嫁人,让我们在文字中感受世俗的关怀和温情的同时,进一步领悟到对逆境中个体生命尊严的尊重和关怀才是真正的关怀。《生命是美丽的》写老师以温情和关怀让学生领悟生命的美丽,篇幅虽短,撒下的却是一抹人性之美的光辉。《老人与鸟》写人鸟之间的深情,对人性之善和生命之温情作了诗意的表达。而《杀人者》则鞭挞人性中丑恶的一面,以悲剧的结局对人性之善和心灵之净化发出了呼唤。上述这些作品和意蕴与之相近的其它一些作品,共同组成了李永康小小说的温情风景线。在这道风景线上,心灵的净化和精神的慰藉在文字中平实地闪烁着,将作品的人文关怀和风一般吹进了读者心里。
值得注意的是,在表现上,上述作品的温情与关怀并不是靠平面的累叠来营造,而是通过一定的空间对映来展现的。李永康在他的文字中构筑了两个互相映衬的情感空间:悲情的空间和温情的空间。这两个空间既是作者笔下人物生活的世界,也是作者向我们提供的审美平台。有了这两个空间的对映,作者不仅顺利地进入了笔下人物的内部,同时也顺利地将冲突引入了读者的内心,使镶嵌于文字中的悲悯情怀在阅读中自然地凸现出来,完成了对温情和关怀的艺术表达。《生活》中“我”设想的王玉梅的命运和其实际命运的对映,《生命是美丽的》中“我”与学生所处的环境和其内心世界的对映,《杀人者》中人心的单纯和复杂、人性中美和丑的对映……,都让作品产生了一种内在的对称和张力,让作品在平衡、朴实的结构中有了跳动。不过,这种结构并不是其作品的全部风貌,在对温情和关怀进行直笔表现的同时,李永康也尝试以曲笔来表现。《孤独的夜晚》便是这样的作品。主人公在街头无聊地闲逛,无所事事中,“他”开始恶作剧地拨打一些电话。作者在小说中并没有直接写“他”内心的孤独,然而结尾淡淡一句“他不忍心伤害这样的女人”,让主人公的内心跳出了单纯的恶作剧心理而一下立体了。表面看来,这篇小小说似乎是在揭示现代社会的一些乱象,但究其本质,其实还是指向了作者一直追求的人文关怀。从李永康不同时期的小小说作品可以看出,温情和关怀一直是其创作中一个脉络清晰的母题,它们在涂抹人性光辉的同时,也为李永康的创作凿开了一条文字和心灵交汇的溪流。
但是,也应该看到,由于作者在创作上追求“以平民化的价值观、伦理观,以平民的心态、以平民的眼光、平民的然而也是平民作家的话语来关注那些很普通的人”(见李永康小小说集《小村人》冯辉序),使得其小说的语言和叙述也基本囿于朴实而少了一分意趣,少了一些飞翔的感觉,这也在一定程度上或多或少地影响了其小小说的阅读审美享受。作为一个读者,我希望在李永康以后的小小说作品中,读到叙述和内容结合得更好的作品。
原载《微篇文学》
- 1 温江区文化馆2021年公共文化数字化平台运营及维护服务项目 评选公告
- 2 2025年温江区文化馆市民艺术培训学校(留位艺术夜校)培训服务采购项目 评选公告
- 3 成都市温江区文化馆(美术馆)2025年保安服务采购项目结果公示
- 4 成都市温江区文化馆(美术馆)2025年保安服务采购项目评选公告
- 5 温江区文化馆2024年公共文化数字化平台运营及维护服务项目结果公示
- 6 温江区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目录及 项目代表性传承人 (2024年版)
- 7 温江区文化馆2024年公共文化数字化平台运营及维护服务项目评选公告
- 8 2024年温江区文化馆市民文化艺术培训学校服务外包项目结果公示
- 9 “成渝地•巴蜀情”——“成渝德眉资”文旅交流联动暨2023年“成都文化四季风•音乐消夏”少儿才艺大赛五城市总决赛我区7人获奖!
- 10 2024年温江区文化馆市民文化艺术培训学校服务外包项目评选公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