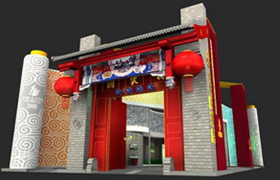读完《小村人》这本小小说集子,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李永康独特的叙述方式。他总是把概述压缩到最少,以场面、细节这些最为生动和形象的描写方法,沿着一条清晰的时间的线索,平心静气又悟性深深地一路倾诉自己心中的块垒。纵览其50余篇作品,李永康实在是太长于这种以生动的场面描写来说话了。在我的记忆中,不少小小说作家是用概述来叙述的,很容易使作品读起来太像一个由精明的文学院的学生们编写的“精典作品故事梗概”了,干巴,枯燥,没有一点文学形象可言。
李永康不这样。他的描写有一个倾向,那就是没有所谓的“艺术化”的痕迹,而是尽量逼真化,接近生活的原生态。
在开始他的描写之前,往往有一个不普遍、却也值得一说的特点,那就是他有时会以一句话来做引子。《酒干倘卖呒》第一句话是:“如果不打官司,他还不知道出事的真正原因。”此后,故事全部由翔实、丰满的小场面构成。这些小场面是连贯的、自然的,好像一个个蒙太奇镜头。《老人与鸟》开头是:“每天早晨,我都见一位老人骂骂咧咧地来到阳台上。”然后是一连串动态的画面,流水一样把这个内蕴凄楚的故事叙述出来。《小村人》这样:“曹歪嘴后来的结局是小村人做梦也想不到的。”
他的这句开篇话,似乎用一般意义上的“概述”来定位又不准确。我们会发现,这句话总是站在“现在”为“将来”而说。我由此想到,在李永康小小说世界的深层,隐藏着一个现代的叙述幽灵。
就是它指引着李永康。
这就是我要说的“其次”:他总是寻找着多种多样的表现形式。除了干干净净、纯粹的场面描写及以一句引子开头的形态之外,李永康还有很多方式来讲述他的故事:《沧桑泪》浓缩了两个人生片断;《四代人的姓名》除了人物对话之外,连半句背景、人物关系、事件起因的交待都没有;《那天晚上的夜好长好长》很像一个剧本…李永康是丰富的,他的小说模式是处于动态变化中的。
李永康不像别人那样只是叙述一个好看的故事。可以说,李永康是非常“看得起”情节的。他总是把他最为重要的东西托付给情节。但这并不就意味着他仅是一个专心叙述或说描写故事的作家。在他那里,故事只是一个可以意会的东西,李永康内心里流动的其实是另一些更加难以言传、却又让他不吐不快的内容。《修壶记》让人几多无奈!一个阴谋原来是这样一步一步眼睁睁地来到我们面前的。《挂历》又有多少让人哭笑不得的东西藏在里面!
在李永康的意念深处,蛰伏着的不是用通常说的“真善美”所能概括得了的,而是现代理性之光烛照之下的人世情态的“写真集”。这种理性表现在,他发现人是生活在夹缝中的,人性受到挤压,理念畸形伸展。我们对这样的生活状态,无法简单地用道德、伦理等评判标准来评说。《挂历》这个尴尬的故事孰对孰错?我们不知道该指责什么。《人之无奈》题目就是无奈的,内容则更加让人不知所措。
李永康的作品还显出深厚的民间生活的功底,突出的表现就是,语言非常的“四川化”。《赌鬼们》有两段对话:
“嗨嗨!你龟儿子又哄我!”
“哟!老子啥时候哄过你龟儿子?”
这种四川化的语言主要被运用于作品中人物的对话上。在这种语言上浮出的是一个个地方特色鲜明的人物形象。
独特而丰富的表现方式,鲜明的人物形象,经典的“四川化”语言……这就让我得出一个结论:一个作家不必去追求什么奇装异服,借以显示自己作品的现代和先锋,只要他认真地观察、深刻地体味人间炎凉,以最深沉的情怀悲天悯人,他就能够使自己的作品显出真正的意义来,获得深层次的共鸣。
这不应该成为一个作家的最大的幸福吗?
(原载《文艺报》2000年7月25日、《四川农村日报》2000年8月12日、收入《小小说的九十年代后》 作家出版社2004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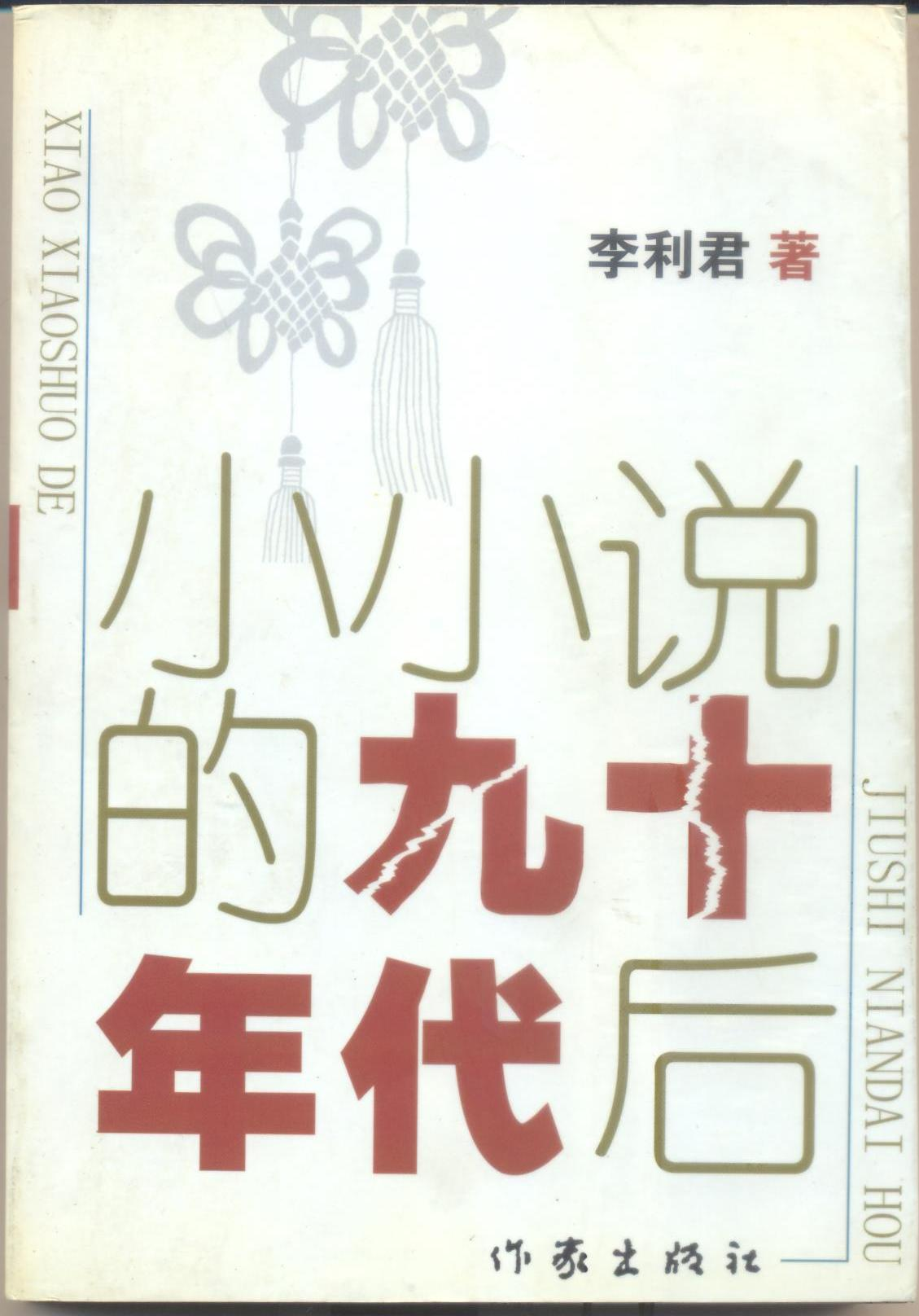
《小小说的九十年代后》 李利君 著 作家出版社2004年
李利君,广东作家,著有小说集《等到天亮》、评论集《小小说的九十年代后》等
- 1 温江区文化馆2021年公共文化数字化平台运营及维护服务项目 评选公告
- 2 2025年温江区文化馆市民艺术培训学校(留位艺术夜校)培训服务采购项目 评选公告
- 3 成都市温江区文化馆(美术馆)2025年保安服务采购项目结果公示
- 4 成都市温江区文化馆(美术馆)2025年保安服务采购项目评选公告
- 5 温江区文化馆2024年公共文化数字化平台运营及维护服务项目结果公示
- 6 温江区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目录及 项目代表性传承人 (2024年版)
- 7 温江区文化馆2024年公共文化数字化平台运营及维护服务项目评选公告
- 8 2024年温江区文化馆市民文化艺术培训学校服务外包项目结果公示
- 9 “成渝地•巴蜀情”——“成渝德眉资”文旅交流联动暨2023年“成都文化四季风•音乐消夏”少儿才艺大赛五城市总决赛我区7人获奖!
- 10 2024年温江区文化馆市民文化艺术培训学校服务外包项目评选公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