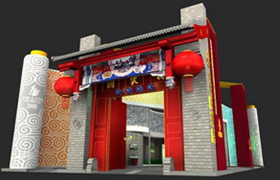摘要:李永康的小小说创作独具特色,巧妙的诗化结构、浓郁的娱乐趣味和深厚的哲理意蕴是其作品突出的审美特征,其创作为小小说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有益的参考和借鉴。
关键词:李永康;小小说;诗化结构;娱乐趣味;哲理意蕴;
据世界华文微型小说研究会秘书长、太仓市作家协会主席的凌鼎年统计,在主要或曾经以创作小小说而加入中国作家协会的90余位当代作家当中,四川李永康是为数不多的具有小小说领域多重身份的作家:工作于成都温江区文化馆的李永康,在1998年就牵头组建了四川温江微篇文学学会并出版《微篇文学》,为推动四川小小说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同时他还积极撰写大量推动小小说发展的评论文章,出版了《小村人》、《生命是美丽的》、《红樱桃》等三部小小说集——“编辑、评论家和作家”的三位一体,让河南省作协副主席、郑州《小小说选刊》总编杨晓敏都认为,李永康“以这种身兼数职‘复合型’的业界角色,多年来活跃在作者和读者的视野里,自然惹人注目。”
本文不对李永康的编辑方针和评论文章作过多论述,而是把目光集中于李永康的小小说作品,因为国内专门研究小小说的湛江师范学院刘海涛教授就曾指出,李永康“能形成自己突出的小小说的个性和风格。”[2]。我们纵观李永康的小小说作品,会清晰地发现其呈现出三个突出的特征:巧妙的诗化结构、浓郁的娱乐趣味和深厚的哲理意蕴。这些特征不仅使李永康在当代小小说作家群中成为一个独特的存在,同时也为当代小小说进一步实现繁荣发展,提供了某些思考和路径选择。因此,我们研读李永康的小小说,应当如著名作家阿来所言的读李永康的小小说那样,“要特别心无旁鹜,而不能因其篇幅的精短而带上吃快餐的心态。”
一、巧妙的诗化结构
阿·托尔斯泰说过:只有好的结构才能使小小说作品成为一个完整的东西。但同时,“小说可以有各种各样的作法,不一定要讲故事,不一定要有头有尾,不一定要有高潮有结局,不一定要布局曲折动人。”[1]小说的这种诗化结构,我们在20世纪中国文学中即可清晰察知。无论是现实主义流派文学研究会,还是浪漫主义流派创造社;无论是蛰居北京的京派作家群,还是沉醉上海的海派作家群,一大批小说作家诸如庐隐、淦女士、郁达夫、郭沫若、沈从文、废名、汪曾祺等,都是抒情小说的代表人物。而汪曾祺在论及新笔记小说(即小小说——笔者注)时也说,“依我看,小说是一种生活的样式或生命的样式。那么新笔记小说可以说是随笔写下的一种生活,一种生活或生命的样式。”[2]
笔者不是很清楚李永康除了写小说外是否还写散文和诗歌,但笔者可以肯定的是,李永康是喜欢散文和诗歌的,正是这种喜欢,会潜移默化于文字精悍短小的小小说作品中,并使笔下的小小说具有一种散文特征的诗化结构。具体来说,他的小小说诗化结构是建立在以下情形基础上的——故事性并不强,也就是说故事结构框架并不缜密,但思维空间却大大拓展;情节要点四处可见,却被发散的抒情意味涵盖其间;叙事功能明显弱化,人物性格依赖意境来彰显。因此,在李永康的小小说中,以情节为中心的叙事结构被以环境等为中心的叙事所替代,因为小说中的“叙事”,“在中国古代最早称为‘序事’,不仅有讲述的意思,而且暗示了时空顺序,隐藏着思维的多元性,包含了异常丰富的文体乃至文化哲学内涵。”[3]
但或许,“非情节性的细节、场面、印象、梦幻等,反而容易体现作家的美学追求”[4]我们可以看到,李永康小小说中的诸多非情节性的表达,是建立在擅长于对传统文学精华的吸纳和对现代文学经典的涵括。无论是《两棵树》对树的拟人化描写,还是《生命是美丽的》中肆意铺陈的情感宣泄,抑或是《十二岁出门远行》中心理活动的极力展示,以及《路》、《女教师与蝎子》、《红樱桃》、《美的诞生》、《善与真》等作品,都是巧妙地运用了多种表现手法来奠基诗化叙事结构:故事情节淡化,而意识流式的散文特征非常明显。看似小小说,有情节有人物有细节描写,但却又像是散文,形散神不散。在他的作品里,散文和小说的区分似乎难以界定,但却能让人体悟到一种经典美文的无限张力。当然,我们不要忘记这种来自诗化结构的张力,是建立在他对题材的特殊处理之上的。
关于对题材的处理,李永康显示出对生活的独特感悟与得心应手的撷取。纵观李永康小小说的题材,大体来说,主要有以下几类:一类是关注乡土炊烟的乡下人。“对于被放逐者来说,故乡不属于他们。于是,有家难归,乡思转化为乡愁。”[5]关注乡土题材,其实可以看做李永康对故土的思念。比如:对知识有不同认知角度的兄弟俩(《兄弟》),从来不曾迟到却为了学生永远迟到的黎老师(《迟到》),来自贫寒山区的乡村小姑娘王玉梅同样渴望平等渴望尊严(《生活》),风雨几十年依然爱国爱民爱家的将军(《将军树》),不喜欢城里而愿意生活在老屋的五奶奶(《五奶奶》),等等。这其实是“游子归乡”母题的拓延。一类是关涉世态炎凉的城市底层,如为免啤酒瓶爆炸而回收空酒瓶的善良秉性的“他”(《酒干倘卖无》),热爱文学的知天命老人(《作家》),想到郊区吃一餐渣渣面的张三李四(《代价》),一直渴望互相做次生意的A 与B(《机会》),真情反被无情误的“笔者”(《老板不知道的》),等等。一类是瞩目于自然风物与人文社会类,如风景区两棵特别的松树,在风雨几十年后两种不同结局(《两棵树》),微型小说发展趋势中的微型小说(《关于微型小说的微型小说》)等。
“在新时期小说中,带有明显的目的性的叙述不多见了,代之而起的是叙述的过程性。在叙述事件的进展时,作者往往把许多与事件无关的小插曲写了进来。”[6]李永康的小小说中的这种小插曲是很多的,如《十二岁出门远行》中“我”在路上的那些飘渺而散漫的思绪。但是小小说文体的字数要求(一般为1500 字左右),又不得不将这种插曲细化到一些少量字句,以保证整个作品的通顺、精炼和简洁,如《沧桑泪》表现三代人思想观点的是少量的文字,特别是“笔者说他是瞎子就是瞎子!”非常明了。汪曾祺说过“小小说比抒情诗更具情节性的那么一种东西”,由此可见,“小小说”与“抒情诗”在结构上有着某种内质的对接,即发散思维与淡化情节。
二、浓郁的娱乐趣味
众所周知,大众文化是当代中国的最大文化背景,娱乐趣味是大众文化异彩纷呈的秘密之所在,也是大众接受大众文化的原因之所在。小小说作为与中国大众文化同时勃兴的文学新体类,一定程度上又不能不被大众文化所影响,从而呈现出四个明显的对应关系,即:大众文化的普及性和小小说的大众化、大众文化的消费性和小小说的市场化、大众文化的娱乐性和小小说的趣味化、大众文化的渗透性和小小说的渗透化[7]。而小小说的娱乐趣味,又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内容表现上的幽默而使作品显得“幽趣”,一个是在情节表现上的反转而使作品显得“乐趣”,一个是语言表现上的巧妙而使作品显得“妙趣”。纵观李永康的小小说,我们可以获知其作为一位深谙传统文化的作家,是不拒绝在作品中表现“幽趣”、“乐趣”和“妙趣”的。
一是其“幽趣”是建立在内容的幽默之上的。其中对作家的调侃成为其中最大的亮点。辛辛苦苦自费出版的书,无处售卖,只好采取到书店寄卖的形式,最后才知道销售如此之好乃是因为老伴不忍心见其痛苦而选择偷偷地购买(《理解》);“笔者”为什么能成就为一个获得很多文学奖励证书的作家,那是因为“笔者”深谙花钱就能“获奖”的缘由(《笔者是一个获奖专业户》);杀猪的“胡屠夫”千辛万苦出了本书,并请专家题写了序言,可意外的是“老者”认为除去那篇名家序言其他还是能看看的(《胡屠夫出书》)。当然,对一些社会世现的“揭露”也是其“幽趣”的展示内容之一。“有事就打手机”的潜台词背后是“手机”是人情世故的缩影,关键时候能帮得上忙的永远都是自己的亲人(《手机手机》);改造积极而又擅长作秀的“陈平”不仅让同时落魄的知识分子看不上,就连领导也看不上他(《绝招》);标榜为作家的A、B、C、D,在讨论如何才能创作出好作品时,却对一位真正的乞讨者冷眼相看(《可怜》);“李老师”的儿子不想上大学,认为再努力最终也是混个饭碗,而镇上的王经理、张董事长却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考上大学,他们认为人生最大的遗憾就是“肚子里没有多少墨水”(《怪圈》)。这些在内容幽默中显示出一种“幽趣”的作品,本身就是幽默的,甚至有时凸显出一种苦涩味。
一是其“乐趣”是建立在情节的反转之上的。在古代章回小说中,悬念和高潮是其主要
特征,往往每到高潮之际,小说嘎然而止,“要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留下一个悬案让读者揣摩。而在小小说里,悬念和高潮往往都集中于结尾。也因此,“欧·亨利式结尾”成为一部小小说好看耐读的最佳模式。因为这种结构常常让读者心理情境发生出人意料的变化。从前述的“的诗化结构”可以观之,李永康的小小说似乎与“欧·亨利式”结构有些绝缘,但作为小小说的情节之间的娱乐趣味却又自始至终在呈现。读五年级的儿子和笔者在街上坐车时,在三轮车上发现了一个书包,好心好意找到失主时,被告知这是一个诚实测试(《书包》);女教师最后才知道男友为什么离开自己,原来是男友在乡村小学的那个夜晚被蝎子蛰过(《女教师与蝎子》);做了父亲的“他”和孩子在大街上散步,望见前面蹒跚走路摔倒的老人说是瞎子,而最后的结果是那老人却是自己的父亲(《沧桑泪》);客车上抢位置的小伙子,在大家的笑声中后知道让座给后面的大娘(《笑浪里的苏醒》);姑娘分文不要地在养殖场养猪,当女主人怀疑她有什么动机辞退她后,发现对方原来是一个农业科技工作者(《娟娟》);“笔者”在大街上买挂历碰到了老同学,邀请去他家坐坐时信口说了句送挂历,哭笑不得地把挂历送给了挂历多如牛毛的老同学(《无言的结局》)。
一是其“妙趣”是建立在语言的巧妙之上。“文学作为一门语言的艺术,其文学价值的实现和语言是密不可分的”[11],在小小说中更是如此。粗糙的语言既不会给读者带来审美享受,也不会引导读者进行深入的思考、得到深刻的体验。所幸李永康是非常注重语言的凝练,体现了一个有责任感的作家对读者的重视。如《沧桑泪》表现三代人思想观点的是少量的文字,特别是“笔者说他是瞎子就是瞎子!”充满着一种无奈和自负;《美的诞生》对一个购书人的描写,细致却又并不张扬;《将军树》里排比式的短句,刻画着一位生于斯长死于斯的伟大将军;《杨子荣》里首尾照应式的简练,诠释着一位善良朴实的农民;《机会》中A 与B的心理对话,质朴而又意蕴深远;《岁月》中对话式结构解剖着一代代围城人;《特别通行证》里简单的对话就揭露了社会的阴暗面;等等。当然,李永康在某些作品中也毫不吝啬语言的铺陈,甚至有的作品显得有些“啰嗦”,但这些看似累赘的语言,在增强作品结构诗化功能的同时,也深刻地刻画着主人公的性格和作品价值的凸显:《十二岁出门远行》,以一个孩童的视角,懂得了亲情与友情,也懂得了父辈之间简单而又厚重的爱情,更懂得了成长的历程;《无言的结局》里诸多细节描写,展示了人性根底的善与恶。
因此,我们会发现,李永康作品中的娱乐趣味,其实都源于他对生活的深切体会,作为一个在1987年就开始发表小说的作家来说,生活的感悟是他创作的根源,他不会为了创作而去创作,也因此他小小说中所透露出来的娱乐趣味,必须经过读者认真细致地品味和反复不断地揣摩。
三、深厚的哲理意蕴
”优秀的文学创作离不开对文学的诗性特质的个性化理解和执著的艺术信念、离不开明确的历史意识以及人本哲学之思的独到体验和感知;诗、史、思的有机融合,是文学创作的一种理想境界”[12]据了解,李永康的很多小小说作品都被《读者》、《作家文摘》、《小小说选刊》、《微型小说选刊》等转载,甚至有的作品被介绍到了国外。由此可见,李永康的小小说创作,可以说就是这样一种诗、史、思的有机融合:“诗”是指其诗性表达,“史”是指其世态关注,“思”是指其哲理意蕴——影响的建立或者说成绩的彰显,是通过作品深厚的哲理意蕴来体现的。
李永康作品中的哲理意蕴往往是通过“暗示”、“双关”与“象征”予以体现的,可以说,李永康是一个善于运用修辞手法的作家,但他又对修辞手法表现为一种拒绝状态,即他不会铺陈修辞,而是在字里行间隐露出来,从而达到“借一斑略知全豹,以一目尽传精神”的美好意境。《两棵树》是作品集《红樱桃》的开篇之作,笔者认为这篇文章的重要性远远超过作为文集标题的《红樱桃》。《两棵树》的两棵树都是松树,在它们都还是松果子的时候,它们都渴望落在好土里生根发芽,遗憾的是它们分开了:一颗生长在好土里,一颗生长在悬崖上。面对不同的生存环境,它们都有着强悍的生存毅力,但天意作物,长在好土里的水桶粗状松树在一个黑夜的风雨里匍匐在地,而那颗悬崖峭壁上的松树却在风雨中昂首挺立。其实人生又何尝不是呢,逆境与顺境的区别永远都不是一成不变的,只有扎根大地,才有可能长久地仰望星空。
《路》里的“笔者”在奋斗多年后明白了一个道理:人人都有一条成功的路在等着你,关键在于你是否有足够的信心找到它。而这样的道理,又何尝不是每一个成功者的现实总结呢?!《不可预料》中的“他”作为班主任,坚持对学生一视同仁,而不是依据哪位家长的过分热情。而当“他”收下家长们送的礼物后,结局只有两个:要不继续坚持己见,要不走向人生悬崖。《善与真》中的“爷爷”,一直相信善有善报的传统伦理,也因此他能在八十九岁去世时,“他走得很安详”。《机会》是一篇不可多得的优秀文章,“A”和“B”就如现实中我们的每一个人,总是希望朝着理想走,却又在理想的半路上歇下脚来等候,最终的结局也许是“A”和“B”几十年一直没有合作过,“A 和B 的遗言没有人能听明白”。
此外,李永康作品中的哲理意蕴还在于其对题材的选择。在第一节“诗化结构”中,笔者曾从题材选择这样一个侧面分析过诗化结构的建立基础。但扫描李永康所有的小小说,会发现他喜欢在作品中建构一种感情距离,缔造一个情感空间,而这不仅是作品的主要亮点之一,同时也是哲理意蕴的又一典型附着物——因为现实语境中,人的存在总是逃离不了“情”的藩篱。在《二胡的悲剧》、《爱的荒漠》、《爱笔者的人已经飞走了》、《成都初恋》、《二十年之约》、《黑蝴蝶》、《岁月》等一系列爱情题材的作品里,得出这样一个结论:爱情应当恰到好处,希望在合适的时间合适的地点遇见合适的人,否则一切都是一种错误的搭配。这种爱情观也衬托出一种别样的哲理意蕴,即远与近,多与少。《二胡的悲剧》不是物品“二胡”的悲剧,而是人的悲剧,这种悲剧可以让那所音乐学院的老师蹉跎不已,也更让“笔者”在面对真正爱情的时候缺乏一种魄力,虽然这种魄力在年少无知时往往都会缺少,但“笔者”失去的不仅是爱情,还有一个纯真女孩一生的幸福。《爱的荒漠》里的艺术家让《二胡的悲剧》里的故事没有再上演,艺术虽然高于生活,但艺术终究是来源于生活,当面对来客“凤妞”的一番话,艺术家终于明白了艺术的真谛和爱情的真谛。遗憾的是,《爱笔者的人已经飞走了》和《黑蝴蝶》里的“笔者”并非都是艺术家,现实中的我们永远都是跟着感觉走,在这种感觉走的过程中抛弃了爱情,以及在美妙故事过后的凄然结局(《成都初恋》)。不过人生或许永远都超脱不了现实的羁绊,关键是在烦恼人生和一地鸡毛中如何把握自己的人生走向,《二十年之约》和《岁月》告诉了我们,过好每一天,人生的哲理意蕴永远都是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之中,把握现在也就把握了未来,当然也就把握住了属于自己的幸福。而一旦在人生之路上走错了方向,那么可以预知的结果将会一无所获(《别一路车》)。
前面笔者就提到过,李永康是一位“三位一体”具有多重身份的作家,在面对小小说(微型小说)的发展路径上,他在《关于微型小说的微型小说》和《二十世纪末微型小说界一场将起未起的官司》中,似乎对当前小小说创作状况和作家创作环境进行了一个颇有意味的关注和深入内心的思考——无论是作家创作作品,还是作家面对形形色色的质疑,都因为社会的不可预知性和现实生活的复杂性。但作为作家不应当只是在这种现实迷雾中保持缄默甚至堕落,而应当给社会大众指引某些方向,为人民提供更多的具有精气神的诗、史、思有机融合的优秀作品。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跨越前进,当代小小说也进入了一个蓬勃发展的重要时期。压力与动力总是形影随行,机遇的存在同时也意味着挑战的潜伏。小小说发展也面临着诸多“精品意识欠缺”、“小小说难出成果”的质疑和焦虑。但笔者相信,无论现实社会多么复杂,作家创作环境多么糟糕,李永康都将会继续走下去,因为从他作品中,我们看到了一个坚定的李永康,一个独立的李永康,一个将诗化结构、娱乐趣味和哲理意蕴内化于作品之中的李永康。作为一个作家,有自己的创作风格,有自己的写作思想,有自己的努力拼搏,就足以证明他会在创作之路上越走越稳健。笔者相信,如果大多数作家都能做到这一些,那么小小说将在文学百花园里呈现的面貌,将不仅仅是一枝独秀的奇葩,而将是一个异彩纷呈的“大观园”,真正成为“当代文学的一道风景”[9],真正做到“小小说连接大世界”[10]、文坛飞出‘金麻雀’”[11]。
注释:
[1]陈平原.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102.
[2]汪曾祺.新笔记小说选·序[M].北京:作家出版社,1992.
[3]龙钢华.弘扬民族的叙事话语——评赵炎秋、陈果安、潘桂林著《明清叙事思想研究》[J].
湖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2).
[4]陈平原.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131.
[5]陈平原.在东西方文化碰撞中[M].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87:144.
[6]庞守英.新时期小说文体论[M].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1997:277.
[7]张春.百花园里的一朵奇葩——当代大众文化背景下蓬勃发展的小小说[D].湖南师范
大学,2007.
[8]吴培显.诗、史、思的融合与失衡——当代文学的一种反思[M].北京:中国文联出版
社,2001:33.
[9]张春.小小说:当代文学的一道风景[N].人民日报,2009-3-26.
[10]金光.小小说连接大世界,“小小说节”在郑州举行[N].人民日报(海外版),2009-6-15.
[11]刘先琴、董一鸣.文坛飞出“金麻雀”——小小说现象透视[N].光明日报,2009-6-30.
(原载《湖南工业大学学报》2011年1期、《中国小小说六十年》 张春 著 湖南大学出版社2012年12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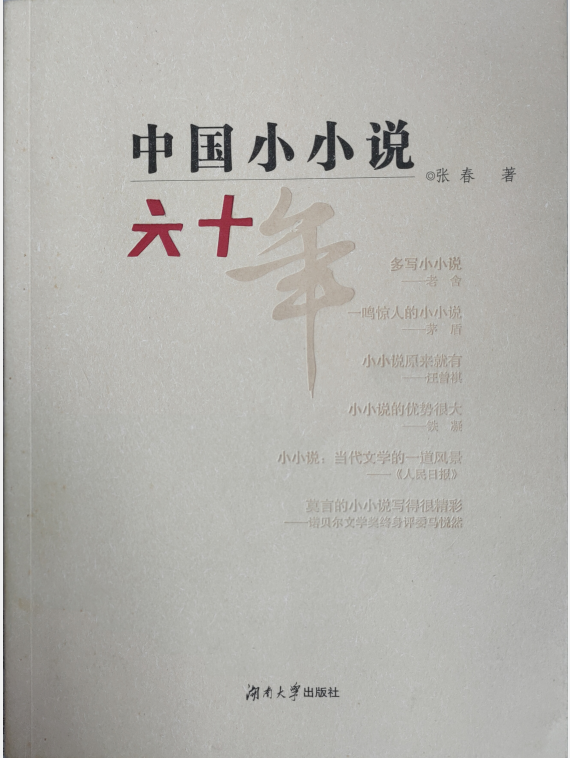
此文题为《李永康小小说论》收入《中国小小说六十年》张春 著 湖南大学出版社2012年12月

此文原载《湖南工业大学学报》2011年1期
张春(1979—),男,湖南永州人,湖南工业大学副教授,博士,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和影视传媒。著有《中国小小说六十年》等。
- 1 温江区文化馆2021年公共文化数字化平台运营及维护服务项目 评选公告
- 2 2025年温江区文化馆市民艺术培训学校(留位艺术夜校)培训服务采购项目 评选公告
- 3 成都市温江区文化馆(美术馆)2025年保安服务采购项目结果公示
- 4 成都市温江区文化馆(美术馆)2025年保安服务采购项目评选公告
- 5 温江区文化馆2024年公共文化数字化平台运营及维护服务项目结果公示
- 6 温江区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目录及 项目代表性传承人 (2024年版)
- 7 温江区文化馆2024年公共文化数字化平台运营及维护服务项目评选公告
- 8 2024年温江区文化馆市民文化艺术培训学校服务外包项目结果公示
- 9 “成渝地•巴蜀情”——“成渝德眉资”文旅交流联动暨2023年“成都文化四季风•音乐消夏”少儿才艺大赛五城市总决赛我区7人获奖!
- 10 2024年温江区文化馆市民文化艺术培训学校服务外包项目评选公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