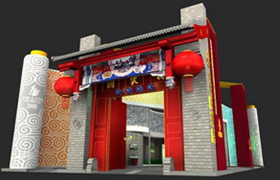在我国小小说文体的建设中,有那么一个人的贡献显然是忽略不了的——作为作家,他写出了《生命是美丽的》、《十二岁出门远行》等小小说佳作;作为评论家,他策划采访了杨晓敏、许行等人的访谈;作为主编,他把《微篇文学》这份小刊物办出了大境界。把这三者紧密地缠绕在一身的人是谁呢?他就是四川的李永康,一种新文体的忠诚实践者、热心推动者和积极传播者。
一:新文体的忠诚实践者
之所以称李永康是小小说的忠诚实践者,是源于他对这种文体的痴情。李永康说:“我写小小说,是因为此乃是我要做的非同一般之事情中的一件”(见其小小说集《小村人》“代后记”)。从这句话里可以看出,他不是抱着“玩”的心态来创作的,他是把小小说当作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件事情,当作他生命里的一种追求。所以,正如罗伟章评价的那样,李永康从不乱写什么。在浮躁之气笼罩着的日益功利化的文学生态中,他则平静地,扎扎实实地写着他钟情的小小说。这样的态度怎么可能创作不出优秀的作品呢?《生命是美丽的》、《十二岁出门远行》、《红樱桃》、《老人与鸟》等一批小小说佳作在李永康的笔下源源不断地流淌出来,那实在是太自然不过了。
作为一种文体的忠诚实践者,李永康在小小说创作上有着强烈的文体意识。无论是内容还是形式皆是如此。从内容上讲,李永康多是书写社会和人生中美好的一面,从而去展示人性中的真与善,让人们在关怀和温暖中体味生命的美丽。如《酒干倘卖唔》,它以一个老人近于“神经质”的行为,表现了个体生命的被珍视和被维护;再譬如《红樱桃》,文中那个纯真、无邪的小男孩肯定会在我们的心底挥之不去,因为他就是“真”的象征、“善”的化身;最具代表性的一篇当然要数《生命是美丽的》,这篇被广为传播的小小说确实是难得的优秀作品。尽管文章的基调有些沉重,但它散发出来的依然是清新俊朗之气。它告诉我们,生命的花朵从不因贫穷而干枯,向着美丽绽放是生命之花的本质所在。类似的作品还有《小村人》、《将军树》、《迟到》等。
李永康为何把笔墨多放在对社会和人生中美好的一面书写上呢?原因可能有很多。但我想,其中一个多少会与文体意识有关。笔者曾在一篇文章中,把小小说比喻成小说森林中的香樟树。意思是说,小小说也有类似于香樟树的功能:散发香味和驱虫效用。由于小小说的受众群体主要是青少年(以中学生为主),所以它应更多地表现真善美,从正面唤起他们对美好生活和美好事物的追求。如果过多传递人性中阴暗的东西,对尚缺少辨别能力的学生来说,很可能会是一种无意的伤害。作为一种文体的忠诚实践者,我想,李永康肯定比笔者更为明白其中的道理。当然,这并不是说李永康完全不去表现社会和人生中丑恶的一面,《胡屠夫出书》、《挂历》就是对商人和为官者在金钱和权力下被异化的绝妙讽刺,《地球还原公司》则以大胆夸张的方式表达了作者对地球被人们的现实利益日益侵蚀深重忧虑。
从形式上讲,李永康的文体意识亦很强烈。综观他的小小说,特别是近几年来的作品,每一篇字数基本上都控制在1500字左右(现在是被广大作家和读者接受的数字)。虽然从字数上要求一个作家的创作有点荒唐,但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尤其在一种文体的建设过程当中,这种对规矩的遵守可以起到示范和导向作用。除了字数控制大体适宜外,李永康的小小说情节完整,在叙述方式上也多采取线性叙述,从而使得故事清晰,有始有终,人物鲜明,阅读起来十分流畅。李永康强烈的文体意识还表现在他决不把小品文、小故事、小笑话等拉入到小小说的队伍中来,他可以汲取这些文体的优长,但决不会把它们混为一谈。这比起那些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把小小说写成小故事、小笑话的人,无疑又让人们对他多了一份敬意。
或许有人会提出,李永康也写过不少具有实验意味的小小说啊,如《探监》、《误读》、《关于小小说的小小说》、《一场将起未起的官司》等。但从整体上说,这些作品只占很小的比例。因此,它不能从根本上动摇李永康对小小说的忠诚实践。恰恰相反,这些文体实验作为对文体的一种有益补充,正好从事物的另一面延续了他对文体的忠诚。
二:新文体的热心推动者
在1996年第5期的《青年作家》上,作家李永康发表了《小小说的创作呼唤大手笔》一文。在这篇文章里,李永康指出:重复已有的成果是小小说创作的一个误区,也是小小说缺乏大气磅礴的立意的致命缺陷。据说刚刚开始创作小小说不久的侯德云看了这篇文章,产生了很大的精神压力。但我想,这篇文章在当时未必起过多大的反响。不过它很可能由此开始把另一个身份加到了一个作家身上,这就是:新文体的热心推动者。
称李永康为小小说的热心推动者,绝对名副其实。在杨晓敏先生的《小小说是平民艺术》面世后,李永康对此是异样的惊喜,同时也感到不满足,在访谈录中,他说,平民艺术的概念太宽泛了,小小说的独特性又在那里呢?杨晓敏先生的回答是极为精彩的。这就是《再论小小说是平民艺术》的催生。小小说是同时具有三种艺术功能的文学品种:即大多数人都能阅读,大多数人都能参与创作,大多数人都能从中直接受益。今天这个论述被广为引用。其后,李永康还写了文艺随笔《平民艺术的现实意义》等。这是一个读者对一个作者的回应,同时也是一个评论家对另一个评论家的诠释。可以说,正是有了这样的回应和诠释,“小小说是平民艺术”的理论才得以不断地补充和完善,并日渐在人们心中生根发芽。
除了撰写文艺随笔为小小说摇旗呐喊,李永康还策划并亲自操作了杨晓敏、许行、王奎山、谢志强、凌鼎年、罗伟章、滕刚等十多位作家的访谈。这是一个大工程。它需要耗费一个人很多的精力,从某种意义上说,它还是一件吃力不讨好的事。但李永康显然没有顾及这些,他以勇往直前的精神,去做着一个小小说的热心推动者所应承担的责任。结果没让人失望,李永康的这些访谈在小小说领域产生了巨大反响,并在整个小说界也产生了不小的轰动。作为一种系列成果,《为了一种新文体——作家访谈》(中国文联出版社2007年2月出版)在小小说界具有开创性。
李永康的系列作家访谈有以下几个特点:一、它探讨的是有关小小说的重大问题,如小小说的立意,创作数量和质量的关系,大陆小小说存在的不足,海外华文小小说的发展现状,小小说金麻雀奖的设立以及小小说能否进入鲁迅文学奖等,而对小小说的创作技巧、技法等具体、细微的东西,李永康则很少涉及。这固然是因为千变万化的技巧、技法很难在短的篇幅里剖析透彻,更重要的因素是上述问题直接关系到小小说的生死存亡。为了一种新文体的健康发展,李永康不得不作出某些取舍。二、作者的态度是真诚而严肃的。在每一篇访谈的字里行间,我们都可以强烈地感受到,李永康的态度是极为真诚的,他始终像朋友一样不断地肯定(不是附和)着被访谈者,并对被访谈者(如陈永林)遭受某些非议表示理解。这是一种多么良好的美德啊。当然,肯定别人并不意味着无原则的夸奖或吹捧。在关涉到小小说文体的重大问题上,李永康是严肃的。有时因为意见相左,他会撕下脸面据理力争。如对王奎山提出的“读书是一件十分危险的事”上,李永康就以茅盾、王安忆、张炜为例加以反驳。三、作者的视野是宽阔的。虽然是就小小说文体展开的访谈,但作者并不把问题局限在小小说上。因为,作为一个作家,李永康深切地认识到,倘若把小小说封闭起来,那么这种新文体就永远不会有成熟的那一天。所以,在访谈中间,除了引用我国短中长篇小说作家对创作的见解,他还多处引用格里耶、黑井千次、卡尔维诺和《小城畸人》、《米格尔大街》等外国的作家、作品来展开论证。这不是卖弄,这是一个小小说的热心推动者为了文体建设不断努力的体现。
三:新文体的积极传播者
倘若论及小小说文体的传播,《百花园》、《小小说选刊》和《微型小说选刊》无疑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它们使“小小说”这三个字遍地生根,四处开花。不过,还有两份期刊也功不可没,这就是《小小说出版》(原为《小小说俱乐部》)和《微篇文学》。提到《微篇文学》,李永康自然就又浮出了水面。但这次,他不是以作家和评论家的身份出现的,他是作为《微篇文学》的主编来到我们面前。
《微篇文学》创办于1998年11月,每两月一期。刚开始是四开八版小报,后改为对开四版大报。已坚持九个年头,出报51期。至今它还在出,还是李永康在做主编。而且,我还知道,这份小刊物现在办出了大境界。《贡嘎山》、《文学报》近期都作过专题报道。一份小刊物为何受到那么大的重视呢,它究竟有什么特色?
笔者认为,《微篇文学》的特色就在于它对小小说文体的传播,而李永康就是小小说文体的积极传播者。
2003年的10月,笔者收到了一封来信。写信人是李永康。他在信中说:“今天成都一朋友打电话来告诉我,说你在网上告诉了通联方式。因忙,很难上网,朋友又在电话中细细说了。今试着寄几份报纸给你,盼望能得到你的批评指正。还有什么吩咐,请尽管说。都爱好小小说,未见面也是好朋友。”
“都爱好小小说,未见面也是好朋友”。多好的一句话啊,它把小小说人的心紧紧地牵到了一起。碰到这样的主编,有谁不肯去关注《微篇文学》呢。
《微篇文学》对小小说文体的传播,表现在一是扶持新人,刊发其小小说作品;二是刊发小小说理论、批评文章。毫不夸张地说,《微篇文学》现在已成为小小说理论、批评的重要基地之一。近几年它发表了大量文章,如徐肖楠的《中国小小说的生命意识与无边挑战》、叶橹的《袖珍世界里的斑斓——读滕刚的微型小说》等。另外,及时反映我国小小说领域的各种动态,也是《微篇文学》的重要内容之一。这样做的目的,就是为了使更多的人了解小小说,热爱小小说,把小小说这种新文体传播的更远更广。
总之,为了小小说文体建设,李永康无论在创作、评论还是创办期刊上都作出了自己的贡献,从而为小小说发展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用一种新文体的忠诚实践者、热心推动者和积极传播者来评价他,实在不算过分。
(原载《互为观照的镜像》河南文艺出版社2007年2月,《微篇文学》2003年7——9月,)
- 1 温江区文化馆2021年公共文化数字化平台运营及维护服务项目 评选公告
- 2 2025年温江区文化馆市民艺术培训学校(留位艺术夜校)培训服务采购项目 评选公告
- 3 成都市温江区文化馆(美术馆)2025年保安服务采购项目结果公示
- 4 成都市温江区文化馆(美术馆)2025年保安服务采购项目评选公告
- 5 温江区文化馆2024年公共文化数字化平台运营及维护服务项目结果公示
- 6 温江区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目录及 项目代表性传承人 (2024年版)
- 7 温江区文化馆2024年公共文化数字化平台运营及维护服务项目评选公告
- 8 2024年温江区文化馆市民文化艺术培训学校服务外包项目结果公示
- 9 “成渝地•巴蜀情”——“成渝德眉资”文旅交流联动暨2023年“成都文化四季风•音乐消夏”少儿才艺大赛五城市总决赛我区7人获奖!
- 10 2024年温江区文化馆市民文化艺术培训学校服务外包项目评选公告